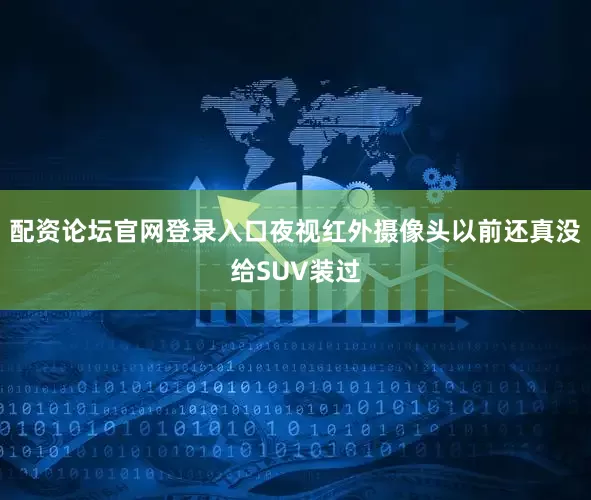张学良幽禁照:赵四小姐一个眼神,让老蒋心里发毛
一张老照片,黑白的,摄于1947年的秋天,地点是台湾新竹。照片里那个男人,腰杆挺得笔直,衬衫袖子随意地卷到胳膊肘,脸上挂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洒脱。他就是张学良。
他身边的女人,赵一荻,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赵四小姐,正亲密地挽着他的手臂。她穿着一身利落的西裤,嘴角那抹笑意,淡得像水墨画里的远山,却藏着一股子韧劲。
“都别动啊,相机要闪了!”旁边端着冲锋枪的守卫压着嗓子喊了一句。咔嚓一声,时间就这么定格了。这张照片,后来在台北的军法署档案室里,一压就是几十年,直到九十年代才重见天日。

要咂摸出这张照片里的味儿,咱们得把时间往前倒拨十年。1936年西安那场大戏唱罢,张学良以为护送蒋介石回南京,这事儿就算翻篇了。谁能想到,飞机一落地,他就被宪兵直接架走,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囚徒生涯。
最开始,赵一荻是以“秘书”的身份跟着。外头风言风语多难听,她全当耳旁风,收拾行李时,就往里头塞了一本日记本,心里就一个念头:跟着汉卿,刀山火海也得走下去。
囚禁的日子,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迁徙。从南京的麒麟宫,到奉化溪口,再到湖南郴州,最后是贵州修文的阳明洞。那地方,山里头湿气重得能拧出水,院墙比屋檐还高,哨兵的皮靴踩在石板路上,咯噔咯噔,单调得让人心里发慌。

张学良在日记里写“此心无风无雨”,说白了,就是绝望了,日子过得跟一潭死水似的。可赵一荻偏不信这个邪,她硬是把这潭死水搅活了。她学着当地人织布,研究怎么煲一锅好汤,在院子角落里种南瓜。她甚至从卫生院借来一本王阳明的《传习录》,陪着张学良一句一句地背。
那些看管他们的军统特务,起初都憋着坏笑,觉得这位娇滴滴的赵四小姐,哪儿吃得了这种苦。可一年后再看,她袖子上补丁摞补丁,人却不见憔悴,那些笑声也就自己憋回去了。
这中间,有个绕不开的人物,于凤至。张学良被关起来的头几年,是这位原配夫人四处奔走,陪在身边。她是大帅府明媒正娶的,身份摆在那儿,谁都得敬三分。可她也看得明白,老蒋心里那根弦绷得紧,对张学良的东北旧部忌惮得很,短期内绝不可能放人。

1940年,于凤至在修文被查出乳腺癌,病情凶险。张学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,只好低头给宋美龄写信求情。戴笠那边点了头,于凤至才得以去美国治病。飞机起飞前,她拉着赵一荻的手说:“汉卿的脾气,你比我更清楚,往后就靠你照顾了。”两个女人对视一眼,话不多,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,就这么交接了过去。
从1941年到1945年,外头打得天翻地覆,重庆的防空警报天天响,几乎没人还记得在贵州深山里还关着个“少帅”。赵一荻陪着他,守着一台短波收音机,听着断断续续的战况。她偶尔会开句玩笑:“人家盼着打完仗能回家,咱们是打完仗也回不了家。”一句话,把所有辛酸都嚼碎了咽下去。
抗战一胜利,周恩来在重庆的政协会议上,公开要求国民政府恢复张学良的自由。这话像是捅了马蜂窝,蒋介石一听就火了。东北那边正乱着呢,这时候要是把张学良放出来,那不是给自个儿添堵吗?老蒋一不做二不休,1946年底,干脆用军舰偷偷把人送到了台湾新竹的井上温泉,一个更彻底的牢笼。

台湾的山林确实漂亮,可再美的风景,隔着铁丝网看,也变了味儿。他们住的日式木屋,窗户又窄又小,白天屋里也昏沉沉的。赵一荻还是老样子,把日子过得一丝不苟。清早起来煮一壶青茶,中午给远在美国的于凤至写信报平安,晚上就在走廊下,借着灯光给张学良理发。
看管他们的特务头子,从戴笠换成了毛人凤。说来也怪,毛人凤对赵一荻倒还算客气。或许是真被这个女人的坚持给镇住了,又或许是他看明白了,张学良已经离不开她,与其刁难,不如省点事。
其实,最熬人的不是物质上的苦,而是见不到儿子张闾琳。1943年,她狠心把孩子送到香港托付给亲戚,从此母子分离,只能靠书信往来。每年中秋,她都会把一块月饼掰下一小角,小心翼翼地压平,夹在信里寄出去。那月饼到了大洋彼岸,早就没了味道,可那份念想,却比什么都重。

到了六十年代,美国《时代》周刊的记者,也不知托了多少关系,居然拿到了探视许可。记者看着头发花白的张学良,问了个所有人都想问的问题:“将军,如果今天您能重获自由,最想做什么?”张学良听了,没说话,只是笑了笑,转头看向身边的赵一荻。那一刻,所有的答案,都在那个眼神里了。
名分这事儿,张学良心里盘算了十几年。1963年,他终于下定决心,给于凤至寄去了一封长信和离婚文件。信里千言万语,最后落到一句请求:“给小荻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吧。”远在纽约的于凤至,收到信后,没有半点犹豫就签了字。后来她跟朋友说:“我信他的判断,也信她的真心。”
1964年1月,台北一个不对外开放的小教堂里,举行了一场极为简单的婚礼。张学良穿着深灰色的西装,赵一荻则是一身墨绿色的旗袍。当牧师问她是否愿意时,她轻声说出“我愿意”,声音不大,却让整个屋子都静了下来。教堂外头,几个军统的人面无表情地守着,整个过程,他们只是记录,不做任何干涉。

从28岁到68岁,赵一荻把一个女人最宝贵的四十年,全部投入到了张学良那扇走不出去的院门里。这期间,他们还一起受洗,成了虔诚的基督徒,信仰成了他们后半生最大的精神支柱。这事儿,还是宋美龄在中间牵的线。
很多人不知道,负责看管他们的特务头子刘乙光,跟张学良的关系很微妙。他既是看守,某种程度上又成了唯一的“朋友”,他的日记里记录了大量张赵二人生活的细节,今天我们能知道这么多,还得感谢他那支笔。
说句实在话,张学良的后半生,在政治上是彻底的失败者。可从个人情感上讲,他又是幸运的。有意思的是,换个角度想,正是因为有了赵一荻这样不离不弃的陪伴,才把一头曾经叱咤风云的“东北虎”,变成了一个安于现状的“居家人”。这无形之中,大大降低了蒋介石看管他的难度和风险。一个女人的爱情,竟成了稳定政敌的最好武器,历史的吊诡之处,莫过于此。
我个人觉得,赵一荻的选择,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爱情。那是一种把自己的人生与另一个人的命运彻底捆绑的决绝。她用一生的陪伴,既成全了张学良,也为自己画下了一个无法被评判的句号。
大财配资-炒股配资论坛-上海配资知识网-股票配资平台代理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